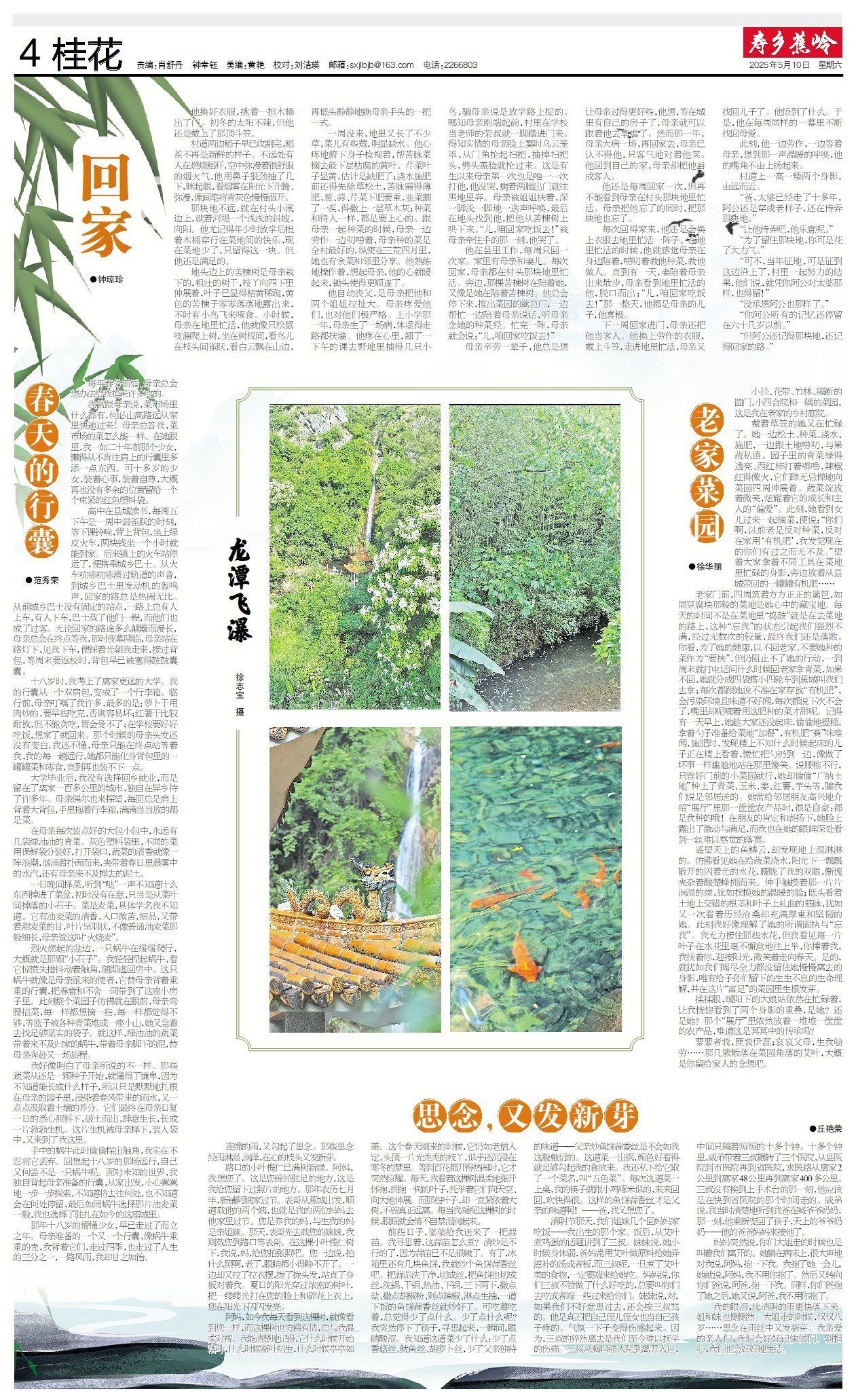
回家
●钟琼珍
他换好衣服,挑着一担木桶出了门。初冬的太阳不辣,但他还是戴上了那顶斗笠。
村道两边稻子早已收割完,稻茬不再是新鲜的样子。不远处有人在燃烧稻秆,空中弥漫着很舒服的烟火气,他用鼻子狠劲抽了几下,眯起眼,看烟雾在阳光下升腾、弥漫,像画笔将青灰色慢慢洇开。
那块地不远,就在村头小溪边上,就着河堤一个浅浅的斜坡,向阳。他尤记得年少时放学后担着木桶穿行在菜地间的快乐,现在菜地少了,只留得这一块。但他还是满足的。
地头边上的苦楝树是母亲栽下的,粗壮的树干,枝丫向四下里伸展着,叶子已显得枯黄稀疏,黄色的苦楝子零零落落地露出来,不时有小鸟飞来啄食。小时候,母亲在地里忙活,他就像只松鼠吱溜爬上树,坐在树杈间,看鸟儿在枝头间雀跃,看白云飘在山边,再低头静静地瞧母亲手头的一把一式。
一周没来,地里又长了不少草,菜儿有些蔫,明显缺水。他心疼地俯下身子检视着,帮苦脉菜摘去最下层枯腐的黄叶。芹菜叶子显黄,估计是缺肥了;浇水施肥前还得先除草松土,苦脉需得薄肥,葱、蒜、芹菜下肥要重,韭菜割了一茬,得撒上一层草木灰;种菜和待人一样,都是要上心的。跟母亲一起种菜的时候,母亲一边劳作一边叨唠着,母亲种的菜是全村最好的,纵使在三荒四月里,她也有余菜和邻里分享。他熟练地操作着,想起母亲,他的心就暖起来,锄头使得更顺遂了。
他自幼丧父,是母亲把他和两个姐姐拉扯大。母亲疼爱他们,也对他们极严格。上小学那一年,母亲生了一场病,体虚得走路都扶墙。他疼在心里,翘了一下午的课去野地里捕得几只小鸟,骗母亲说是放学路上捉的。哪知母亲刚端起碗,村里在学校当老师的荣叔就一脚踏进门来。得知实情的母亲脸上霎时乌云笼罩,从门角抡起扫把,抽掉扫把头,劈头盖脸就抡过来。这是有生以来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他,他没哭,瘸着两腿出门就往黑地里奔。母亲被姐姐扶着,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迭声呼唤,最后在地头找到他,把他从苦楝树上哄下来。“儿,咱回家吃饭去!”被母亲牵住手的那一刻,他哭了。
他在县里工作,每周只回一次家。家里有母亲和妻儿。每次回家,母亲都在村头那块地里忙活。旁边,那棵苦楝树在陪着她,又像是她在陪着苦楝树。他总会停下来,推出菜园的篱笆门,一边帮忙一边陪着母亲说话,听母亲念她的种菜经。忙完一阵,母亲就会说:“儿,咱回家吃饭去!”
母亲辛劳一辈子,他总是想让母亲过得更好些,他想,等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了,母亲就可以跟着他去享福了。然而那一年,母亲大病一场,再回家去,母亲已认不得他,只客气地对着他笑。他回到自己的家,母亲却把他当成客人。
他还是每周回家一次,但再不能看到母亲在村头那块地里忙活。母亲把他忘了的同时,把那块地也忘了。
每次回得家来,他还是会换上衣服去地里忙活一阵子。在地里忙活的时候,他就感觉母亲在身边陪着,唠叨着教他种菜,教他做人。直到有一天,妻陪着母亲出来散步,母亲看到地里忙活的他,脱口而出:“儿,咱回家吃饭去!”那一整天,他都是母亲的儿子,他喜极。
下一周回家进门,母亲还把他当客人。他换上劳作的衣服,戴上斗笠,走进地里忙活,母亲又找回儿子了。他悟到了什么。于是,他在每周同样的一幕里不断找回母爱。
此刻,他一边劳作,一边等着母亲,想到那一声温暖的呼唤,他的嘴角不由上扬起来。
村道上一高一矮两个身影,由远而近。
“爸,太婆已经走了十多年,阿公还是穿成老样子,还在侍弄那块地。”
“让他侍弄吧,他乐意呢。”
“为了留住那块地,你可是花了大力气。”
“可不,当年征地,可是征到这边沿上了,村里一起努力的结果,他们说,就凭你阿公对太婆那样,也得留!”
“没承想阿公也那样了。”
“你阿公所有的记忆还停留在六十几岁以前。”
“但阿公还记得那块地,还记得回家的路。”
春天的行囊
●范秀荣
每年春分前后,母亲总会想办法给我捎来许多吃的。
我常跟母亲说,菜市场里什么都有,何必山高路远从家里快递过来。母亲总答我,菜市场的菜怎么能一样。在她眼里,我一如二十年前那个少女,懒得从不肯往肩上的行囊里多添一点东西。可十多岁的少女,装着心事,装着自尊,大概再也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一个个束紧的红色塑料袋。
高中在县城读书,每周五下午是一周中最雀跃的时刻,等下课铃响,背上背包,坐上绿皮火车,两块钱坐一个小时就能到家。后来镇上的火车站停运了,便搭乘城乡巴士。从火车吭哧吭哧滑过轨道的声音,到城乡巴士里发动机的轰鸣声,回家的路总是热闹无比。从前城乡巴士没有固定的站点,一路上总有人上车,有人下车,巴士载了他们一程,而他们也成了过客。无论回家的路途多么颠簸而漫长,母亲总会在终点等我,那时夜幕降临,母亲站在路灯下,见我下车,便踩着光朝我走来,接过背包,等周末要返校时,背包早已被塞得鼓鼓囊囊。
十八岁时,我考上了离家更远的大学。我的行囊从一个双肩包,变成了一个行李箱。临行前,母亲叮嘱了我许多,最多的是:萝卜干用肉炒的,要早些吃完,否则容易坏;红薯干比较耐放,但不能贪吃,胃会受不了;在学校要好好吃饭,想家了就回来。那个时候的母亲头发还没有变白,我还不懂,母亲只能在终点站等着我,我的每一趟远行,她都只能化身背包里的一罐罐菜和零食,直到再也装不下一点。
大学毕业后,我没有选择回乡就业,而是留在了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城市,独自在异乡待了许多年。母亲偶尔也来探望,每回总是肩上背着大背包,手里拖着行李箱,满满当当放的都是菜。
在母亲每次装点好的大包小包中,永远有几袋绿油油的青菜。灰色塑料袋里,不同的菜用保鲜袋分装好,打开袋口,蔬菜的清香就像一阵浪潮,汹涌着扑面而来,夹带着春日里晨雾中的水汽,还有母亲来不及掸去的泥土。
一日晚间择菜,听到“哒”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掉进了菜盆,初时没有在意,只当是从菜叶间掉落的小石子。菜是麦菜,具体学名我不知道。它有油麦菜的清香,入口微苦,细品,又带着甜麦菜的甘,叶片呈羽状,不像普通油麦菜那般细长,母亲管这叫“火烧麦”。
烈火燃起的盆边,一只蜗牛在缓缓爬行,大概就是那颗“小石子”。我轻轻捏起蜗牛,看它惊慌失措抖动着触角,随即逃回房中。这只蜗牛就像是母亲派来的使者,它替母亲背着重重的行囊,把春意和不舍一同带到了这座小房子里。此刻整个菜园子仿佛就在眼前,母亲弯腰掐菜,每一样都想摘一些,每一样都觉得不够,等篮子被各种青菜堆成一座小山,她又急着去找足够坚实的袋子。就这样,绿油油的蔬菜带着来不及归家的蜗牛,带着母亲脚下的泥,替母亲奔赴又一场旅程。
我好像明白了母亲所说的不一样。那些蔬菜从还是一颗种子开始,就懂得了谦卑,因为不知道能长成什么样子,所以只是默默地扎根在母亲的园子里,浸染着春风带来的雨水,又一点点汲取着土壤的养分。它们最终在母亲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,破土而出,肆意生长,长成一片勃勃生机。这片生机被母亲择下,装入袋中,又来到了我这里。
手中的蜗牛此时偷偷探出触角,我实在不忍将它丢弃。回想起十八岁的那场远行,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蜗牛呢。面对未知的世界,我独自背起母亲准备的行囊,从家出发,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探索,不知道将去往何处,也不知道会在何处停留,最后如同蜗牛选择那片油麦菜一般,我也选择了驻扎在如今的这座城里。
那年十八岁的懵懂少女,早已走过了而立之年。母亲准备的一个又一个行囊,像蜗牛重重的壳,我背着它们,走过四季,也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,一路风雨,我却甘之如饴。
老家菜园
●徐华丽
小径、花带、竹林、隔断的圆门,小四合院和一隅的菜园,这是我在老家的乡村庭院。
戴着草笠的她又在忙碌了。她一边松土、种菜、浇水、施肥,一边跟土地唠叨,与果蔬私语。园子里的青菜绿得透亮、西红柿打着嘟噜,辣椒红得像火,它们肆无忌惮地向菜园四周伸展着。蔬菜绽放着微笑,炫耀着它的成长和主人的“偏爱”。此刻,她看到女儿过来一起摘菜,便说:“你们啊,以前老是反对种菜,反对在家用‘有机肥’,我发觉现在的你们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望着大家拿着不同工具在菜地里忙碌的身影,旁边放着从县城带回的一罐罐有机肥……
老家门前,四周筑着方方正正的篱笆,如同豆腐块那般的菜地是她心中的藏宝地。每天的时间不是在菜地里“捣鼓”就是在去菜地的路上,这种“忘我”的状态引起我们强烈不满,经过无数次的较量,最终我们还是落败。你看,为了她的健康,以不回老家、不要她种的菜作为“要挟”,但仍阻止不了她的行动,一到周末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老家拿青菜,如果不回,她就分成四袋搭小四轮车到蕉城叫我们去拿;每次都跟她说不准在家存放“有机肥”,会污染环境且味道不好闻,每次都说下次不会了,嘴里却呢喃着用这肥种的菜才甜呢。记得有一天早上,她趁大家还没起床,偷偷地提桶,拿着勺子准备给菜地“加餐”,有机肥“粪”味难闻,施肥时,发现楼上不知什么时候起床的儿子正在楼上看着,慌忙把勺扔到一边,像做了坏事一样尴尬地站在那里傻笑。说腰椎不行,只管好门前的小菜园就行,她却偷偷“广纳土地”种上了青菜、玉米、姜、红薯、芋头等,骗我们说是邻居送的。她常给邻居朋友高兴地介绍“展厅”里那一筐筐农产品时,很是自豪:都是我种的哦!在朋友的肯定和表扬下,她脸上露出了激动与满足,而我也在她的眼眸深处看到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。
遥望天上的鱼鳞云,却发现地上湿淋淋的。仿佛看见她在给蔬菜浇水,阳光下一瓢瓢散开的闪着光的水花,朦胧了我的双眼,惭愧夹杂着酸楚蜂拥而来。伸手触摸着那一片片润湿的绿,犹如抚摸她的温暖的脸;低头看着土地上交错的根茎和叶子上虬曲的筋脉,犹如又一次看着历经沧桑却充满厚重和坚韧的她。此刻我好像理解了她的所谓固执与“忘我”。我无力接住那些水花,但我看见每一片叶子在水花里毫不懈怠地往上举,你撑着我,我扶着你,迎接阳光,微笑着走向春天。是的,就犹如我们竭尽全力都没留住她慢慢离去的身影,唯有给子孙们留下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理解,并在这片“富足”的菜园里生根发芽。
揉揉眼,暖阳下的大娘姑依然在忙碌着,让我恍惚看到了两个身影的重叠,是她?还是她?那个“展厅”里依然放着一堆堆一筐筐的农产品,难道这是冥冥中的传承吗?
蓼蓼者莪,匪莪伊蒿;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……那几簇散落在菜园角落的艾叶,大概是你留给家人的念想吧。
思念,又发新芽
●丘艳荣
连绵的雨,又勾起了思念。那些思念经雨淋湿、润泽,在心的枝头又发新芽。
路口的小叶榄仁已满树新绿。阿妈,我想您了。这是您曾经驻足的地方,这是我给您留下过照片的地方。那年农历七月半,新铺阿姨家过节。表哥从蕉城出发,顺道载他的两个姨,也就是我的两位妈妈去他家里过节。您是养我的妈,与生我的妈是亲姐妹。那天,表哥先去载您的妹妹,我则载您到路口等表哥。在这棵小叶榄仁树下,我说,妈,给您拍张照吧。您一边说,拍什么照啊,老了,眼睛都小得睁不开了。一边却又拉了拉衣摆,拢了拢头发,站直了身板对着我。夏日的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叶,把一缕缕光打在您的脸上和碎花上衣上,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阿妈,如今我每天看到这棵树,就像看到您一样,而这棵树也仿佛有情,总与我温柔对视。我能清楚地记得,它什么时候开始落叶,什么时候新叶初生,什么时候亭亭如盖。这个春天刚来的时候,它仍如老僧入定,头顶一片光秃秃的枝丫,似乎还沉浸在寒冬的梦里。等到百花都开得热闹时,它才突然惊醒。每天,我看着这棵树温柔地张开怀抱,拥抱一树的叶子,托举着它们向天空、向大地伸展。而那些叶子,却一直紧依着大树,不曾真正远离。每当我凝视这棵树的时候,眼眶就会情不自禁湿润起来。
前些日子,婆婆给我送来了一把蒜苗。我寻思着,这蒜苗怎么煮?清炒是不行的了,因为蒜苗已不是很嫩了。有了,冰箱里还有几块鱼饼,我就炒个鱼饼蒜香丝吧。把蒜苗洗干净,切成丝,把鱼饼也切成丝,洗锅、干锅、热油、下锅,三下两下,撒点盐、撒点胡椒粉、剁点辣椒、淋点生抽,一道下饭的鱼饼蒜香丝就炒好了。可吃着吃着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点什么呢?我突然停下了筷子,寻思起来,一瞬间,眼睛酸涩。我知道这道菜少了什么:少了点香菇丝、鱿鱼丝、胡萝卜丝,少了父亲独特的味道——父亲炒鱼饼蒜香丝是不会如我这般敷衍的。这道菜一出锅,颜色好看得就足够勾起我的食欲来。我还私下给它取了一个菜名,叫“五色菜”。每次这道菜一上桌,我的筷子就跟小鸡啄米似的,来来回回,欢快得很。这样的鱼饼蒜香丝才是父亲的味道啊!——爸,我又想您了。
清明节那天,我们姐妹几个回妈妈家吃饭——我出生的那个家。饭后,从艾叶煮鸡蛋的话题讲到了三叔。妹妹说,她小时候身体弱,爸妈常用艾叶做原料给她弄滋补的汤或者粄,而三叔呢,一旦煮了艾叶类的食物,一定要端来给她吃。妈妈说,你们三叔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,总要叫你们去吃或者端一些过来给你们。妹妹说,对,如果我们不好意思过去,还会挨三叔骂的。他是真正把自己侄儿侄女也当自己孩子疼的。气氛一下子变得伤感起来。因为,三叔的猝然离去是我们至今难以抚平的伤痛。三叔从胸口痛入院到离开人世,中间只隔着短短的十多个钟。十多个钟里,威弟带着三叔辗转了三个医院,从县医院到市医院再到省医院,求医路从离家2公里到离家48公里再到离家400多公里。三叔没有挨到上手术台的那一刻,他应该是在快到省医院的那个时间走的。威弟说,我当时清楚地听到我爸在喊爷爷奶奶,那一刻,他重新变回了孩子,天上的爷爷奶奶——他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了。
妈妈突然说,你们大姐走的时候也是叫着我们离开的。她躺在病床上,很大声地对我说,阿妈,抱一下我。我抱了她一会儿,她就说,阿妈,我不用你抱了。然后又转向你们爸说,阿爸,抱一下我。同样,你们爸抱了她之后,她又说,阿爸,我不用你抱了。
我的眼泪,比清明的雨更快落下来。姐和妹也恻恻然。大姐走的时候,仅仅八岁……思念在雨丝中又发新芽。我亲爱的亲人们,我们会好好记住你们。别担心,我们也会好好地生活。
编辑:李子莹
审核:张英昊




请输入验证码